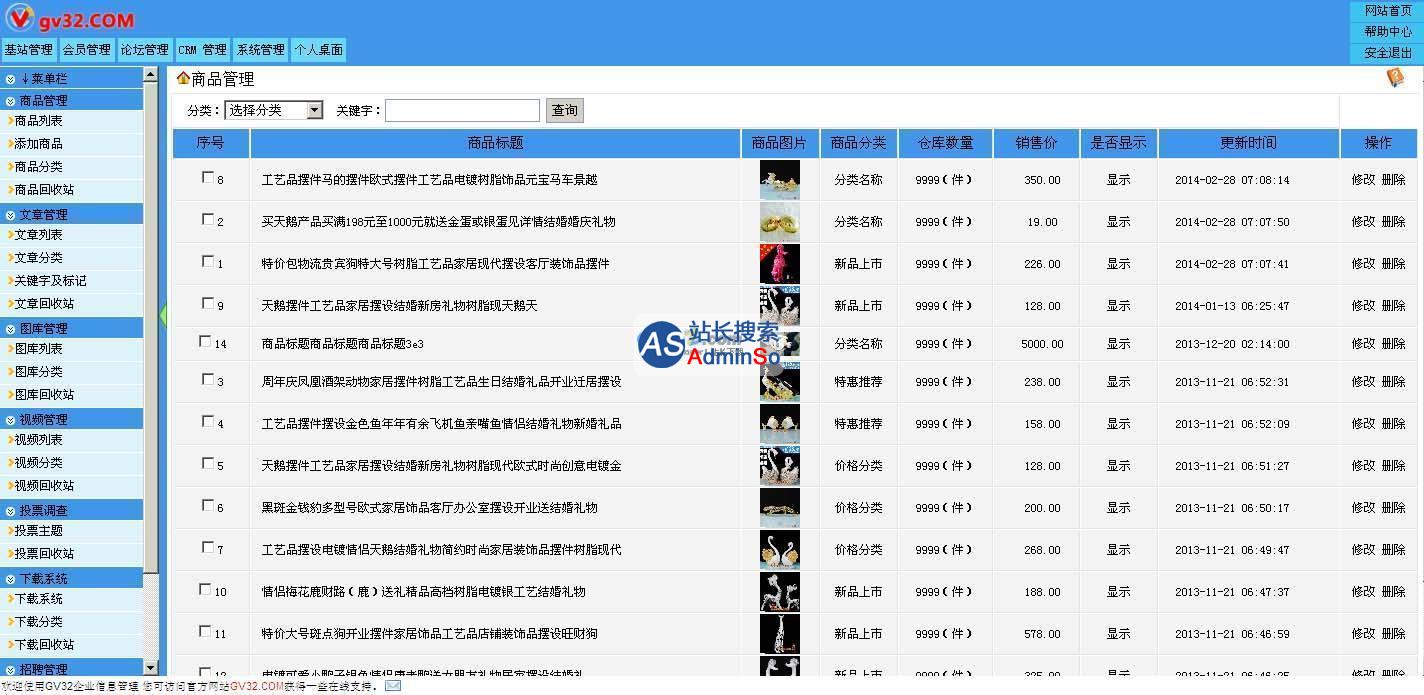人工智能思维-博古睿:智能与智慧: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家
撰文丨新京报记者 董牧孜
一两百年后,或许我们即将迎来奇点,进入强人工智能或超强人工智能时代。很多人对强人工智能怀有生存级别的恐惧感,哲学家、思想家对此也各有说法,我们的思维范式或许还将面临根本性的挑战。
《人类简史》作者、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曾指出,我们不仅仅在经历技术上的危机,也在经历哲学的危机。现代世界的逻辑,建立在17—18世纪的关于人类能动性和个人自由意志等理念之上,如今,这些概念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对于人工智能的不安,普遍比西方人更少。《周易》强调宇宙“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与时偕行、变通趋时的思想沁入了诸子百家,几千年来中国人耳濡目染,成就了中国人对“变”和不确定性的接受,以及开放的人文态度。儒、释、道看待机器人的立场有哪些区别?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在未来仍然有效吗?
新京报记者专访了《智能与智慧: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家》一书的编者宋冰。自2017年年底以来,宋冰所在的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就一些根本性问题,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系列哲学家和人工智能科学家的对谈和工作坊,她在此基础上,编撰了本书。赵汀阳、张祥龙、何怀宏、贝淡宁、李晨阳等哲学家及科学家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回应了上述问题。
宋冰,博古睿研究院副院长、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联席主任。曾长期从事国际证券法与投资银行方面的工作。职业生涯早期,在行政法、竞争法等领域发表诸多学术论文,并编译《美国、德国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等比较法方面的书籍。主编《智能与智慧——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家》。
中国人对人工智能的恐惧,为什么比西方人更少?
新京报:弗朗西斯·福山等学者曾指出,相比西方人来说,中国人面对生物技术等的应用,没有那么多恐惧,往往更为乐观或平常心对待。你是否有类似的体会?这是源于东西方底层逻辑及观念上的差异吗?
宋冰:不少中西人士都注意到,相对于中国人、日本人,西方媒体、知识精英普遍对前沿科技有更多的戒备与恐惧。我没有研究过日本的情况,但是这些年与中国业界、学界的讨论让我认识到,这种不同的态度是有哲学与文化上的原因的。
从西方哲学的主体性角度看,强人工智能的出现使人忧心忡忡。在以人为中心的体系中,主体性强调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与主导性。之于自然、环境、客体化的世界,人是主导者、创造者、塑造者。秉承这种思维的人自然对比人更加“理性”和“智能”的超级智能心存恐惧。但从天人合一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出发,强于人的存在出现并不是问题。
《智能与智慧: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家》,宋冰 编,中信出版社,2020年2月。
新京报:东方哲学的视野,对我们思考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有哪些新启发?
宋冰:“天地人”三才,是中国固有哲学传统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基本思想框架。人存在于天地之间,人道与天道相互贯通融合,人居中可参赞化育。对中国正统社会影响最深刻的儒家思想强调从人的社会性、关系性来认识人,理解人。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中人工智能思维,没有一个抽象的独立于环境与各种关系的假设中的“人”,我们无法脱离天道、地道、人的社会关系来讨论人。这种“关系理性”就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底色。
融入了中国本土文化的佛家思想则在根本的层面上,把人作为形而上本源的作用的体现,在本源作用的层面上,人与动植物是没有根本区别的,都是本源作用的示现,万物一体。在世俗理解的层面上,人不过是众生的一种。由此可见,儒释道在不同程度上秉持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脉络。
虽然儒释道对人生宇宙的本质看法不一、对社会伦理规范各有侧重人工智能思维,但都没有把人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没有把人与自然和其他存在放到一个相互分离、二元对立、征服与零和竞争的结构中。正因为这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一方面很多中国哲学家并不过高估计人类理性;另一方面,把人工智能纳入“仁民爱物”,“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或神仙谱系的讨论框架中也成为可能。和超级智能共处有何不可?这或许是中国人普遍没有如西方人那样产生对超级人工智能的生存级别的恐惧感的原因之一吧。
新京报:相比而言,西方哲学脉络关于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的关注点在哪里?东西方学界对话的基础是什么?
宋冰:当下我看到的大部分西方人工智能哲学方面的研究是关于智能、意识方面的研究。我觉得他们的底层思维还是近代以来占主流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以及主客体的分离等思想。
我觉得中国哲学家和西方哲学家可以在两个层面上沟通对话。一是在对人的本质、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方面讨论、对话。第二,在第一个层次讨论的基础上,就伦理、指导科技发展的规范上进行沟通、对话。如今全球对人工智能规范的讨论大都在第二个层次上。其实是本末倒置了。所以,我一直呼吁我们应该回到哲学的原点,重思何为人、何为物,人物之间关系等讨论,并重思我们的基础价值观。
儒、释、道看待人工智能,立场有别
新京报:儒、释、道对人的理解有所差异,对人工智能的立场也有所不同。儒家的危机感似乎尤为深切,因为人工智能会破坏以血缘及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儒家理论秩序;而道家和佛家则更为坦然。你如何看待这种差异?能发展出儒家的人工智能版本吗?
宋冰:在《智能与智慧:中国哲学家遇见人工智能》一书中,儒家思想家干春松写到,“基因编辑技术和人工方式复制人的行为,会造成巨大的伦理困境,以血缘作为基础的儒家伦理学更是如此。”他十分担心科技手段会造成血缘角色和社会角色的混乱。也有人担心社会引入养老护理机器人会削弱中国传统的孝道,造成更广泛的对老年人的冷漠等等。
当然,儒家思想家中也有积极拥抱前沿科技,乐于将高级智能引入新的扩充的人伦关系中。姚中秋就认为,人类对待人工智能的态度应该是:“人工智能,吾与也,即就像爱自然万物一般。人与人工智能,尤其是强人工智能‘相与’,则可以各自发挥优势,早日成就美善秩序”(第84页)。另一位儒家学者李晨阳甚至认为,或许人类应该“关心、爱护人工智能,将其作为道德行为者或者道德行为的施受着来对待。”(第222页)
道家认为变化和不可预测性是生命的组成部分。王蓉蓉在她的文章中指出,“道家既不拒绝也不全盘接受技术的突飞猛进”。更重要的是技术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关系,加深对道的认识。(第276页)有些道教人士(比方说参加本书写作项目的盖菲)更是异想天开,认为超级智能出现的可能性,会给几千年追求长生不老的道教新启发:或许人工智能可以启发人类通过这一特殊的数字“方术”,终于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第304页)
刘丰河则从大智慧和佛家的视角分析、研判,认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分析能力仅仅是人的相应功能的延伸。人工智能只是人的意识中的概念,人的意识之外不存在这样的概念。刘丰河进一步认为,我们应该超越世俗层面的讨论与争辩,通过思考人工智能与人的问题,进而了悟宇宙人生的真相,那才是人的生命的终极价值所在。(第316页)
所有人工智能的产品和应用都会有不同的应用场景,而适用这些场景的发展和迭代一定会受到设计开发者不同文化价值观和带有文化烙印的学习数据的影响和塑造。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不同文化印记的技术和产品是不言而喻的。比方说,在中国市场设计和开发老人护理机器,就一定应该考虑到孝道,中国社会对隐私的理解和应用也不同于西方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是有可能发展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
新京报:《周易》对于我们理解人工智能的未来方向有什么启发?
宋冰:用中国圣贤的思想重思科学与技术是个方兴未艾的事业。我觉得我们仅仅迈了一小步。我们研究中心也希望聚集更多的思想家,开展这方面的更深入的探讨。
《周易》对人工智能的启发,就我目前粗浅的认识来看,或许更多是在思维方式以及思考伦理规范等方面。中国人普遍没有对超级智能出现生存级别的恐惧,或许也是得益于融入中国人血液中的对“变”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思维方式。
赵玲玲指出,《周易》的行上概念强调,宇宙最终的存在不是静态的某种物质,而是“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的“动”的状态。(第XXIV页)“动”就是变化、不确定性。《周易》的与时偕行、变通趋时的思想沁入了诸子百家,几千年来中国人耳濡目染,也成就了中国人对“变”和不确定性的接受,以及开放的人文态度。这种对变的接受、应变与顺变的处世态度,或许是中国人对无法预测的前沿科技发展轨迹不至于惶恐不安的另一个原因。
赵汀阳尝试用《周易》的“生生”思想为人工智能研发设定边界。他说,“《周易》的‘生生’观念表达了一种未被现代的知识论理性摧毁的存在理性。”“‘生生’的存在理性意味着,人类行为需要一个不可逾越的存在论界限,即只要危及人类的延续,就是不可做的冒险行为。”(第20-21页)
新京报:从同样的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出发,既有对于人工智能的长期发展存疑的思想家,也有保持乐观的思想家。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宋冰:每家思想传统都跨度大、内容丰富。即便是受同一传统影响的思想家,因其视角和侧重点不同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分析。这种视角、分析的多样化在任何领域都是常见的。这也正说明在这一新的哲学与前沿科技融合的思想领域中,大家思想活跃,火花不断,还没有形成所谓主流观点,更没有什么正统学说。这正是思想活力的体现。
另外,我得指出,中国思想家在分析探讨问题时大都也融入了西方哲学的视角。这又是思想多样性的一种表现。中华文明本身就重视不断学习和吸收外来的文化与价值观。这在我们的哲学家群体中表现得十分充分。
中国传统哲学,能帮助我们理解未来吗?
新京报:哲学的产生往往与当时社会发展条件有关,比如儒家思想与传统农耕社会相适应。中国哲学应该拥抱未来,也应该是活的传统。传统的思想模式能在社会结构和技术发生变化的未来,占有一席之地吗?
宋冰:很多哲学思想是在历史的某个阶段产生的,但并不表明它们只适合那个阶段的经济与社会形态。中国人传统的融入自然、与自然相处的智慧,即使在当下高科技数据化的时代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对生命的认识。
儒家思想至今影响着我们对家庭、家人与朋友的相处原则和生活实践。看看西方世界,古希腊产生的民主制度至今还是一个被广泛应用的政治治理制度。当然,同一个概念、制度的内涵、外延可能有了不少的变化,但深层次的思维方式和理念其实变化不是太大。
从传统的思想资源汲取营养,不是为了复古,是为了厘清我们是谁、从哪里来。这样我们才能在固本的基础上兼容并包,吸收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融入我们对当下问题的思索与探讨,发展出融合的、开放的、普世的、应和时代需求的基础性价值观体系。还是一句老话说得精辟、简洁,“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再多说一句,借前沿科技对人类深刻的影响之际,我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一个重思基础价值观的机会,可谓天赐良机。
新京报:在博古睿研究院组织的人工智能科学家与中国哲学家的交流中,人文学者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认知程度是否足够准确?是否存在交流障碍?在科学与人文日益专业化的当下,如何打破不同学科的思维壁垒?
宋冰:我们几代人都是在分科的教育体制中学习、成长、成“家”立业。我们研究中心刚开始把人工智能科学家和哲学家拉在一起时,相互感觉十分陌生,他们对彼此的学术词汇与话语体系完全不熟悉。所以我们做了好几期非公开的科学家与哲学家的对谈。期间,大家都放下“身段”,虚心向对方求教,我们没有“愚蠢”的问题,没有“标准”的答案,只有开放的心胸、求知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通过我们的项目,好几位科学家和哲学家成为紧密合作的学术伙伴。我们希望进一步推进和培育这一新的思想市场的生根、发芽和成长。
我们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中长期的发展趋势对人性和人类社会的影响。这其中难免会依赖于一些科技发展方向和趋势的判断和推演,其中会有些不切实际的假设。但是重要的不是对技术细节的把握,而是思想家们对技术、数字时代下重思对人的定位、对技术发展出超越性智能的认识与态度,以及人类如何思考自身与外在世界的关系。
“全球智库”,如何在当代思想场域中自我定位?
新京报:最后,能否介绍一下《智能与智慧》这本书的缘起?一开始为什么选择用中国哲学切入人工智能这一视角?
宋冰:2017年11月开始,我们在北京大学举办了多场人工智能科学家与中国哲学家的对谈和工作坊,邀请到学界不少在各自领域早已功成名就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参与。在这个基础上,我编撰了《智能与智慧:中国哲学家遇见人工智能》一书。本书见证了他们追求真理,勇于拓展思维的精神,或许这些文章不是这些哲学家和科学家们最擅长的话题或最成熟的思考,但一定是他们挑战自我、突破自我的勇敢尝试。
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第四次科技革命。博古睿中国中心旨在搭建东西方对话桥梁,致力于推动影响人类深刻变化的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项目设置和学者研究聚焦前沿技术和社会治理等领域,目前重点关注前沿科技对人类变革的影响,以及数字治理、全球治理等重要全球性话题。
博古睿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共建研究中心就是希望更多地发展这种融合的研究和探索,搭建起东西方思想家深度探讨和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大的理念框架下,激发中国儒释道哲学家们对前沿科技的关注与讨论以及倡导和培育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人文情怀与哲学素养就成为我们研究院的研究方向之一。
有“全球智库”之称的博古睿(Bergguren)研究院。
新京报:像博古睿研究院这样的“全球智库”,如何定位自己在世界思想场域中的角色?博古睿研究院的中国中心有哪些特色?
宋冰:博古睿研究院总部坐落于洛杉矶,成立于2010年,致力于增进人类对这个变革时代的深度理解,培育和发展新的思想和理念,助力全球各机构、政策制定者以及公众应对影响人类的深刻变化。
博古睿研究院关注人类社会大转型时期的新思想,尤其重视从哲学、文化的视角来理解、分析我们当下面临的挑战与机会,其中就包括前沿科技引起的我们对人性与人类社会组织与管理的理念的重思。同时我们认为,在人类面临重大危机与挑战之际,东西方思想资源的合力或许可以帮助人类走出困境。所以我们的研究方法是力图打破学科之间、人文与科技之间、东西方之间等各种界限和分割。
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于2018 年12 月19 日正式成立。中心由博古睿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共同发起,办公地点位于北京大学校园内。中心吸引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来共同研究、理解人类面临的变革与挑战,发展并分享他们的新思想。中心研究人员和访问学者关注前沿科技和治理创新等主题,特别是人工智能与基因编辑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数字治理和全球化等议题。博古睿研究院承诺投入2250 万美元用于中心建设,包括设立“博古睿学者”项目,举办学术讲座、学术研讨会,支持学术出版、制作多媒体传播产品以及其他项目活动。
新京报:您的背景似乎也相当“跨学科”,在加入博古睿研究院之前,主要长期从事法律和银行工作,曾任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盛中国业务首席运营官和总法律顾问。能谈谈您的工作经历与现今工作的关系吗?
宋冰:基本没有关系。我一直对这些大问题保持好奇心,也特别希望有机会学习并参与思考这些问题。过去两年多,我就是边学、边做、边思考。我的观点很多十分不成熟,甚至有些“不着调”。只能说我还在路上,也会一直在路上。感谢各位海涵,来听我讲我们刚起步的一些尝试。
撰文丨董牧孜
编辑丨董牧孜 校对丨赵琳


 上一篇
上一篇